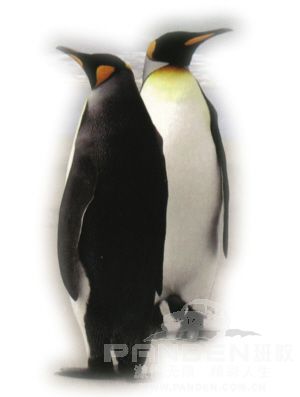



1 谁也斗不过魔鬼西风带
每一次起飞,都缩短着与南极的距离;每一次降落,都令我兴奋不已!
2008年12月14日上午11点,飞机徐徐地降落在地球上最南端的火地岛。一走出机舱,顿时像进入天然的大氧吧,空气清新极了。周围那绵延起伏的雪峰,使我想到青藏高原,不同的是,青藏高原海拔四五千米,高寒缺氧,令人望而生畏;而这里的海拔仅仅10米,呼吸起来,身心舒爽。
我们12月10日从长春起程,先后倒换了4次航班,到香港,到法国巴黎,到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丽斯,飞行40多个小时,航程2.7万公里,今天终于来到世界最南端的港口城市——乌斯怀亚。
下午4点钟,我们登上挪威“前进号”破冰船。它是用特殊厚度、高张力、耐低温的钢材制造的,并配备强大的动力引擎,可以在一米多厚的坚冰上冲撞破冰前进,并且有抗摆系统以降低船身的摇晃。我们将生死相守九天九夜。
不同肤色的各国客人兴奋地站在甲板上,操着各自的语言,哇啦哇啦兴奋得直叫,尽管谁也不大能听懂都感叹什么,可彼此的心境是相同的。
“前进号”的210位游客来自25个国家。中国从2007年才有游客奔赴南极,而此举的破冰者就是广州极至俱乐部,此行的极至四团14人。迄今,中国到南极的游客不超过100人,我们仍属于“先头部队”。
夜晚早已降临,天还大亮着,因为夏日进入了高纬度地区,我们再也看不到彻底的天黑。今晚,我们将过第一道鬼门关——德雷克海峡。风暴一直是这里的主宰,一年365天,风力平均8级以上。人们称之为“魔鬼西风带”、“咆哮西风带”、“死亡走廊”。
各就各位后,领队让大家马上吃晕船宁,躺下睡觉,让西风带在睡梦中通过。
这一觉,我睡得一塌糊涂。可能是晕船宁发挥了药力,还可能是过于疲倦的缘故,以至队友大陈说:“真的有些不吐不快呢!”
这样侥幸的话说不得,最终西风带露出狰狞面目,当感到晕眩时,就来不及了。船左一下、右一下地摆动,人也随之左甩一下,右甩一下,直奔洗手间,“哇”一声,吐得涕泪齐下。中间有间隔,可没几分钟,又大吐起来,直到将胃里的东西吐净,又吐绿色的苦水。
我躺在床上,不敢睁眼,看到什么都会晕眩,都会恶心。眯了一会后,我强撑着起床,很想看一眼大海。海浪到底有多大?西风带到底什么模样?这一看不要紧,又一阵恶心。眼中看到的西风带并不像我想像的那么白浪滔天,而是海面鼓起圆圆的浪头,就像田野刚犁过的一道道深垄沟。据说,这叫浪涌,比白头大浪厉害。
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同程度地晕了,号称铁汉的队员单车王子也两天没露面了。看来,谁都斗不过西风带啊!
2 半月岛:被点穴一样定在那儿
接到15点30分登陆半月岛的消息,心便像揣了小兔子似的,急忙翻出所有防寒防冻防风防雨的装备。冲锋衣、救生坎肩、橡胶水靴,还有一个防水背包,里面装着两部照相机、一部摄像机、一个三脚架、旗帜等。这样一武装,全身的分量真的不轻!
每人脖子上都挂着一张船卡。每次上下船都要刷卡,便于船公司掌握乘客去向。
从大船登汽艇时,要踩在海绵的洗鞋池,之后还有人用水枪冲刷你的裤脚,以防将陆地上的树种、花粉等生物或细菌带到岛上。
三天来一直在大洋上漂泊,满目只有滚滚波涛相伴,突然出现一块白色陆地,那感觉不亚于鲁滨逊漂流到荒岛。
一踏上冰原,我就像被什么点了穴一样定在那里。那不是我千遍想、万遍念的企鹅么?它们在石砬上,在雪丘上,不是1只,不是10只,不是100只,而是成千上万地晃动着,真的像电影里的一样,有的站立着望着我们,有的索性向我们一摆一摆地走来。
那一刻,时空发生了逆转,走动着的不是我们,而是企鹅们。我们呆呆地望着这些“土著居民”,这片岛屿的“主人”,它们却很自如很友好地欢叫着,或奔走相告着。
我激动得不能发声。好一会儿,才缓过神来,脑袋里储存的信息飞快地转动起来。这座岛是帽带企鹅聚居的王国,有上万对之多,眼前的小家伙们就是帽带企鹅了。
仔细一打量,它们头上戴着黑帽子,有一条细绳似的黑杠沿着头顶从脸上画到脖子上,就像戴着警察大盖帽似的;并且它们喜欢大吵大嚷、直颈高歌,走起路来挺胸昂首,真有点儿军人的气派呢!
这些“小帅哥”实在太迷人,害得我几乎不能移步。半月岛绵延2公里,登陆的时间限定1小时,我不能陷在这里,那就不能拜会更多的“小帅哥”了。
看看有人回返,我急忙向前跑,路上的企鹅来不及拍照,只能用眼睛送个秋波了。
3 库佛维岛:挡了企鹅的高速路
我们的冲锋艇在高高低低、大大小小的浮冰中穿行。船开得缓慢,船帮撞着冰块发出喀嚓喀嚓的响声,碰到绕不开的大浮冰,咣当一声震得船身一晃。越临近岛,震动越大。
一踏上库佛维岛,“哎哟”、“快帮忙”的求助声不绝于耳。雪很深,一脚踩不正,就整条腿陷到雪中,必须由别人帮忙才能从深雪中拔腿,不摔几个跟头几乎是不可能。
这个岛是南极金图企鹅最多的地方。计算企鹅数量不是以只,而是以对,因为企鹅只有夏季交配时才会上岸,它们总是成双成对、形影不离。
金图企鹅性情温顺,有“绅士企鹅”的别号。它们的眉毛是白色的,嘴巴是橙色的,脚也是橙色的,简直是化了妆的美少女!
南极公约对人生效,对企鹅就不管用了。冰山上有一只企鹅飞快地向我奔来,我举起摄相机蹲在雪地上,对准这个“小美女”。它跑到我面前忽然停住了,就那么友好地好奇地瞧着我,我有点莫名其妙,不敢声音太大,怕把它吓跑;也不能声太小,怕它听不着。我柔和地说:“怎么不走了?继续走,到我的镜头里来,那样,你就有机会成为大明星!”它还是那么静静地望着我,似懂非懂。我和它,奇妙地对峙着,时间就那么一秒一秒地过去。忽然,我听到有人叽哩哇啦地冲我说着什么,我一看,是个老外,比比划划地打着手势。我忽地明白了,他是让我给企鹅让道,原来,我一激动,就把企鹅高速公路的事情忘了。
我一闪开,企鹅又继续前行,沿着那条无数企鹅踩得很明显的高速公路,旁若无人地走到海边,跳进水里。人们通常奇怪,企鹅怎么那么守纪律,走路总是一个挨一个地排着纵队呢?这回我近距离地一看,就明白了,它们都是沿着自己的路走,就免去了雪地上的深一脚浅一脚的艰难了。
4 威尔米娜湾冰川:冒险拍照
威尔米娜湾是以英国女皇的名字命名的。这里是鲸鱼和海豹进餐的场所,曾经是捕鲸人经常光顾的地方。
驶近巨大的能有几层楼高的折射出幽蓝光彩的冰壁前,顿时风也平了,浪也静了,就像冰川们集结在这里开会,会场静悄悄。一座座奇异的冰川、冰山倒映在清澈的水面,只有我们撞击浮冰的声音划破了这里的寂静。
那冰川近在咫尺,伸手可及。或站或卧或躺或倒,千姿百态,好一群冰雕众生相。
那一块块巨大的冰川从远处看,造型或方、或扁、或矩形、或梯形;而坐在汽艇里近距离地看,就不是横平竖直、简单的线条了。有的像被木梳刮过的条纹,见证着这里风暴的凛冽;有的像万年古树的一圈圈年轮,记载着过去数千甚至数万年的气候变化;有的布满蓝色透明的裂缝,随时都可能四分五裂。
那时,我多么希望自己再长几双眼睛、再长几双手,因为处处是精彩的超乎想像的冰川,闭上眼睛随便拍都将是获奖作品。当然,在冲锋艇上拍摄冰山,谈何容易?那几层楼高的冰山,得仰颏欣赏,广角镜都发挥不了作用。拍摄角度不容选择,你只能坐在艇上,赶上哪儿摄哪儿,为躲避同伴的遮挡,有时不得不冒险探出半个身体。最担心的是,冰川随时有崩塌的危险。小艇上下颠簸,只能不管不顾地胡乱瞎拍一气了。那刻,每个人都闭上了嘴,咔嚓咔嚓就是按快门的声音。
5 希望湾:“南极原住民”
登陆希望湾,明显感到海上风浪的淫威。浪头打来,满脸水花,凉冰冰的,好在很快便顺利靠岸。
远远地,看到几个小孩子跑进小木屋。我以为是来岛上探亲的家属,后来得知,他们都是岛上的居民。
许多国家对南极辽阔的冰原以及它所覆盖的巨大资源垂涎三尺。为了制造话语权,阿根廷竟在20世纪70年代“制造”了一些“南极原住民”——鼓励一些条件出色的夫妇,志愿到南极岛上居住并生儿育女。就这样,1978年,第一个南极人在这个希望岛诞生,成了世界上罕有的“南极原住民”了……
我们走进岛上的小商店,有邮票,有T恤衫。这里的人极其热情,温暖我的不只是屋中间通红的火炉,更有一张张亲切的笑脸。这里不仅地域上没有“国界”,思想中也没有“国界”。据说,各国考察站之间时常“串门”,当一国的科考队员途经另一国的考察站时,休息一下,吃顿饭,更是司空见惯的事儿。南极大陆上还设立了许多避难所,里面放些食品、燃料、通讯器材、御寒服等,门不上锁,各国考察队员以及探险者遇到天气不测,可以自行进住,里面的物品自行取用,不用付款。
我忽然发现靠里面的墙边有一个一人高的小支架,上面放着一个16开的留言簿。我好奇地翻看起来,各国文字,五花八门,都是来这里参观的客人留下的。我情不自禁地拿起笔,在上面写道:向工作在南极的阿根廷科学家致敬!我的签字虽然不起眼,却将中国的方块字挤进众多的各国文字中,也表达了中国人对来南极科学家的景仰和爱戴之情。
6 惊心动魄30分
我是从希望岛最后一批撤下来的。
海上的风浪大起来。海水“哗啦、哗啦”一排排地拍击着岸边,冲锋艇在冰水中晃晃悠悠。人们趟着水登上汽艇,稍不留神,就会被浪头打得站不稳。情况十分危急,这一切早已在船公司的预料之中,只不过为稳定军心,没有向我们通报而已。我一看,来时每个冲锋艇乘坐8人,现在改为6人,就感到问题的严重。
我上汽艇时,一个浪头打来,险些被浪冲倒,冰凉的海水灌满靴筒,顿时不停地打颤。
冲锋艇在大浪的冲击下,不停地摇摆,我们刚刚坐下,驾驶员“腾”地一下将汽艇驶离岸边,他在争分夺秒!
寒冷并不可怕,最可怕的是汽艇在海面像蹦极一样,我无法让屁股稳坐在船上,随着船的颠簸,人一蹦一顿地咣当咣当,随时可能从船上飞出去。为了加强把握住的力量,我将相机包紧紧夹在两腿间,两手紧紧抓住中间的钢管,可这样仍然险象环生,一会儿这边歪一下,一会儿那边歪一下,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,不时会冲撞身边的人。身边恰巧也是位女同胞,她吓得妈呀妈呀地直叫。
恶浪一个跟一个穷凶极恶地打来,成千上万地起伏着,像地狱里的黑色幽灵涌动着,凄厉的风也不怀好意地摇旗呐喊,企图把羸弱的我们抓进无底的深渊。
最为可怕的是,我的手冻僵了,已感觉不到是否握着钢管了,禁不住大声呼救。危急时刻,对面的小麻用戴着手套的双手紧紧按住我的手,才使我有了几分安全感。我不能不这样认为,那时那刻,他就是我的救命恩人。
我从飞溅的浪花的空隙间瞄向冰川,怎么还看不到“前进号”啊?
我又在海面扫视一下,怎么还没个影子?
是不迷路啦?还是冲锋艇搏斗不过大浪,越飘越背道而驰啊?来时没觉得这么远啊?
当我第n次将余光扫过去,发现了“前进号”的影子。那一刻,简直就是人在冰窟窿里看到一丝光亮,就是落水后即将被打捞上来的感觉。
又经过一阵剧烈的颠簸,终于驶到了大船前,揪着的心终于放下。这时,才感到浑身散架了一样疼痛,擦一把满脸咸涩的海水,湿淋淋地登上大船。
在别人的帮助下,我用僵硬的手勉强卸下背包,换下满是冰水的胶靴,已经麻木的脚几乎不能走路了。忽然间有种死里逃生的感觉。
罕见的鲸群:真担心将船弄翻
7 午饭后,船上广播响了:海面发现12条鲸鱼!
我脖子挎上相机,手里提着摄像机,趿拉着鞋就往甲板上跑。
啊,看到了!座头鲸那巨大的圆滚的灰黑色的身姿露出海面,又一个前滚翻扎进海里,丫字型的巨大尾巴划开海面,带起一片如串串珍珠般的水帘,之后又徐徐地隐进海中。
白色的鳍是鲸鱼的桨,在海水里经阳光折射变成蓝色,鲸鱼的肚皮也是白色的,在海里也是蓝色。那一道道蓝光在我们的船边频频穿梭,伴随着很沉闷的吼声,一串水花像蒸汽机喷气一样,窜起七八米高的水柱,之后庞大的鲸头挺出海面。
鲸鱼的头部是椭圆形的,皮表是一层突起的皱褶,有点像古城门上一个挨一个地镶嵌着的铆钉。敦实粗壮的体态足有十三四米长,中间粗,两边细,形似重磅的大炮弹。它在同类中是航空母舰,体重二三十吨。
当鲸鱼齐刷刷地钻进海水,海面出现瞬间宁静的空隙后,那最叫绝的一幕突然爆发了:远处又一片水柱像城市中心广场的音乐喷泉此起彼伏。顿时,人们的眼睛一下不够用了,有人喊:“快,快看,左前方有一片水柱!”接着又有人喊:“哎,左后方一排水柱!”“那边来啦!”“哇,全线飘红!”
鲸鱼这样的庞然大物,不是通常的两三头,不是二三十头而是鲸群!
此情此景,让整个船为之震惊。此时此刻,让所有人为之疯狂。
鲸鱼从四面八方向破冰船聚拢。它们是到这里开会?不然,怎么这么多鲸鱼乘着南大洋的波涛赶向这里呢?
我分析,鲸鱼和人类一样好奇。鲸鱼们发现破冰船,便大呼小叫地赶来观赏,有的竟然淘气地钻到船底,又从船帮钻出海面,惹得众人惊呼一片。那时,真的担心它们一不小心把我们的船弄翻呢!
队友紫良另有看法,他说,鲸鱼正在进行围捕鳞虾的大行动。它们以数以吨计的鳞虾为食,大嘴一张几立方米的鳞虾和海水一起涌进,闭口时,海水从唇须缝中挤出,滤出的鳞虾一口吞下。鲸鱼在洋面上形成巨大的包围圈,像人类捕鱼赶网一样,让鳞虾越缩越密集,再大口大口地吞食。我们的破冰船正巧误入鲸鱼设下的大围场。
穿着黄色冲锋服的船员说,在海上工作十多年,这样庞大的鲸鱼阵容,他们也未曾见过。
所有被晕船所困扰的人们,此时头也不晕了,胃也不翻江倒海了,人们在有点恐惧的兴奋中,早把各种不适抛到脑后。
南极的九天九夜,精彩纷呈,那片白色大陆,成为我今生最遥远的爱!



